|
【推荐语】
从先祖到现代,无数人开垦过的千年丝路,架起了东西沟通的桥梁。大历史背后,有哪些如明珠般璀璨的故事,等待我们去发掘?
【图书信息】
书名:《胡天汉月映西洋》
作者:[中] 张国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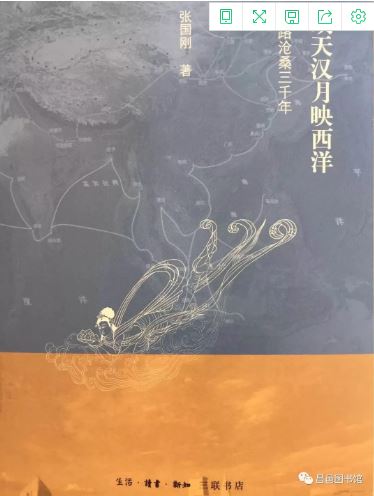
说起丝绸之路的由来,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张骞出使西域呢?
其实早在张骞之前,已经有许多“无名英雄”踏上这条要道了。
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,那个时候,“玉石之路”这个名字更适合用来形容它。
《管子》一书中,多次谈到的“禺氏之玉”,很有可能就是这条通道上的“走私品”。把新疆的玉石贩运到商周王朝疆域内的商人,大多是西戎民族。
可惜,这样的民间贸易没能维持很长时间,秦朝及汉朝初年,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所有道路,贸易自然也被腰斩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丝路沧桑三千年,到了张骞之后,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。强盛的国力和抗击匈奴的成功是最重要的原因。
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后,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也建立起了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,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。
这样的历史也从侧面反映出在丝绸之路上,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的关系。
或者,您也可以这样理解,影响早期丝路畅通的要素不是商品价格,更不是商品的供给与需求,而是中国边疆地域和西部地区的政治关系。
说到这,就不能不提两位对丝绸之路同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古人——班超和甘英。
先来说说班超。
班家两兄弟都是留名青史的人物,班超的哥哥叫班固,是著名的史学家,写下了大名鼎鼎的《汉书》。
哥哥从文,弟弟从武。
公元73年,班超随军出塞,抗击复起的匈奴,没想到,这一去就是近二十年。打退匈奴后,班超受命经营西域地区,巩固汉朝在西域建立的政治秩序。
他成功了吗?
公元91年,一队人马携带着新鲜出炉的任命文书,从皇城出发,奔赴西域。见到班超后,直说恭喜都护。
毫无疑问,班超成功了,西域都护相当于郡太守,是整个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。在他不懈的努力下,西域周边50国全部臣服于汉。
班超却还觉得不够,他派出了一位得力下属,甘英,出使大秦,让汉朝的势力更加深入西域腹地。
然而,大秦可不是一个说去就能去的地方。
在《史记》中,大秦被称为黎轩,如果您还是感觉有点儿陌生,那说到罗马帝国,您大概就熟悉了。
商人不仅在丝绸之路上运送商品、贩卖货物,还能传递远方的消息。
汉朝人听见传闻,说大秦是西域最大的国家,有许多金银奇宝。最重要的是,听说这个国家的国王特别想和汉朝建立外交关系,却总被隔在中间的安息人阻拦。
甘英的出使,如果成功,不仅能直接和遥远的西方大国建立关系,还能打破安息人在中间的垄断地位。
这安息人为什么那么专横呢?
安息人也叫帕提亚人,他们和罗马是一对颇有渊源的对手。为了争夺地中海东部的控制权,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。
所以,安息人可不会轻易就让甘英去到罗马。
每每说起这段历史,学者们都纷纷感叹可惜,安息人竟然用谎言就轻易把甘英给劝退了!
我们来看看安息人说了些什么。
当时,甘英从龟兹,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库车西南出发,经过喀什、莎车,又翻过帕米尔高原,跨过阿富汗,由伊拉克的巴格达东南再向前走,最后“抵支条,临大海”。
关于史书原文里的支条和大海到底指哪里,众说纷纭,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,是在叙利亚西边的地中海沿岸。
奔波了近一年,眼看希望的曙光就在海的另一边闪烁,甘英却突然听到当地的安息人说,没准备好能吃三年的口粮可别轻易出海哦。
这是怎么回事,甘英仔细打听后了解到,这片海域无比宽阔,遇到好风,花三个月就能到罗马,但如果风向不好,在海上飘两年都是正常的。
心里正忐忑不安的时候,又听到有人说,海水有魔法,能让人思恋故乡无法自拔,只能寻死才可解脱,因此丧命大海的人已经数不清了。
地中海真的有那么难过吗?大海真的有杀人的魔力吗?
这些情况我们无从考证,但当时,甘英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,确实打消了渡海西行的念头。
后来,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夏德还大骂甘英是个胆小鬼,被安息人一派胡言就糊弄住了,错失了推动中西建交的大好机会。
也有人指出,不应该全怪甘英,是安息人太精明,想方设法不让汉人访问大秦,以便坐稳自己的垄断地位。
本书的作者张国刚教授却觉得,从汉朝的外交需求来看,甘英出使大秦的政治军事目的大于经贸需求。
所以,甘英也可能是发现遥远的大秦很难被拉拢作为军事盟友,就借安息人的恐吓,顺水推舟选择返程。
甘英虽然没有踏上罗马帝国,但他创下了历史上最远的出使记录,也大大推进了汉人对远西地区的认识。
甘英之后,汉唐时期的中原政权就再没有派遣过这种比较有规模、又留下详细记载的西域外交使团了。
不过,这可不是说没有人出使西方了,还有另一类人,对远方满怀憧憬,我们熟悉的“玄奘西游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玄奘的事迹经过小说家的演绎之后,已然家喻户晓,启发玄奘西行的法显却鲜为人知。
数算历史上远赴西方求法的僧人,法显、玄奘和义净是最成功的三位大师。
其中,法显算得上是西行求法的开创人士。
法显从小就在寺院里做沙弥,二十岁剃度为僧,三十多岁时,来到当时的北方佛学中心——长安。
在佛学造诣不断提高的同时,法显也渐渐发现了佛经有不完备的地方,戒律也有谬误和残缺,就立志要去天竺求经,完善佛法。
在途中,法显创造了许多第一。
首先是年龄最高,他从长安出发的时候已经61岁了。
其次,他是第一个走通中国到巴基斯坦和印度陆上交通的中国人。
如今,在“一带一路”的规划中,法显走过的这段路上,即将建起一条沟通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铁路。
最后,法显为世人留下了名为《佛国记》的著作。书中保留了那个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宝贵记录。
比如,他从斯里兰卡搭乘的商船上有200位乘客,他在苏门答腊岛上逗留了四五个月后,才遇见了能返回故国的商船。
这些信息对我们研究5世纪初叶,南海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商旅航行情况,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。
丝绸之路不仅对历代中国都有重要影响,也影响着西方世界的生活。
随着海陆丝绸通道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,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社会,开始流行一种“中国趣味”的风尚。
从纺织品的花纹、室内装饰到园林景观,欧洲人都喜欢加入中国元素。
安妮女王喜欢穿中国丝绸和棉布制作的衣服。路易十四则热衷于收集中国瓷器和漆器。瑞典国王甚至为王后生日准备了一座木结构的中国式亭子。更别提让英国人沉迷的茶叶了。
可是这一时期的中国,面对的不再是传统认知里,处在朝贡体系中的诸国。
欧洲人也没有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丝绸、瓷器和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超支,这就导致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。
大量白银涌入中国,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,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,甚至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。
种种因素,促使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,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。
经济贸易渐渐演变成了政治和军事冲突……
张国刚老师说,历史是现实永恒的背景。
“一带一路”源远流长。它的背后,也许是帝王夹杂野心和虚荣的政治抱负,也许有商贾怀揣发财梦想的各种算计,也许饱含僧侣追求真理的宗教热情,但更多的,还是众多热血男儿不辱使命、不畏艰险的报国精神。
张国刚老师在这本《胡天汉月映西洋》中,为大家梳理了一遍“丝绸之路”从上古走私通道到如今“一带一路”的演进历程,以及东方文化与异域文化在碰撞交融的过程里,迸发出了哪些华丽的光彩。
丝路上的故事,数不完说不尽,其余的精彩内容就等您亲自走进书里,一一品读了。
|

